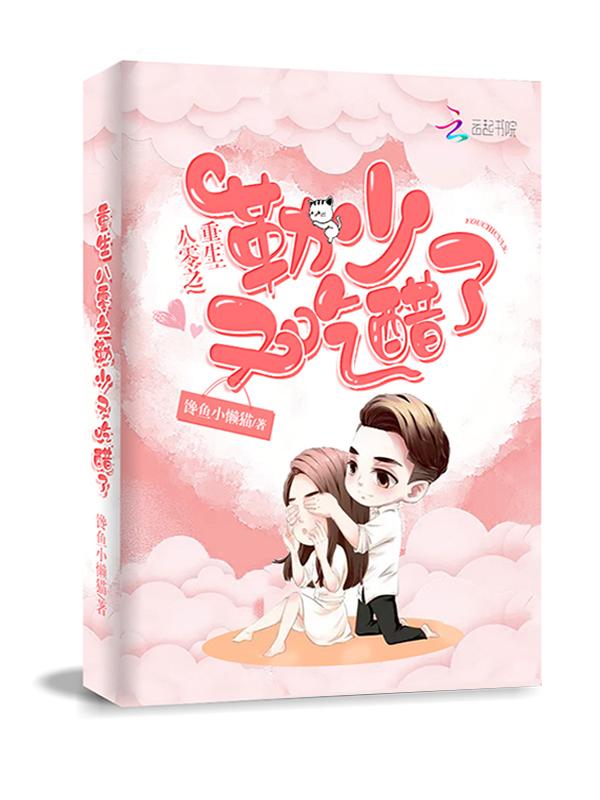文海阁>狐梦 > 第 61 章(第1页)
第 61 章(第1页)
第六十一章
已是深夜时分,胡嬷嬷等吩咐好这里的事,几个伺候的人扶着老人家从雪地里提着灯笼回了自己的院子。
何能看不出她的茸哥儿怕家里这个红发阎王,走时一并将那秦炎喝了出去,命下头的小子先关上院门,夜间有人报时再开。
这里的管事妇人直等到外头街上头一拨巡逻的宵禁卫鸣鼓换班,王爷也未见。
耳室内的紫竹丹青十二扇围屏挡着,香汤烧得,立了小妩几个捧香执水,正侍候小主子洗澡,里头净听是陈乖宝跟爱妹说话笑声儿。
见着实在该睡时,管事的妇人已叫人进去把爱妹撵了,她立在门口,正寻思要不要派人去后头亲家老爷院子里问问时,听得院外墙下小子说话,不多时,平成王身边人打灯笼看路,人总算来了,便迎进来。
进门坐下侍奉了茶水,虽是个王爷,可总也是一副糊涂风流的糟糠作派,这妇人并不怕,跪了叫起,便按事按理禀了夜间的安排,请王爷今夜歇在那边内室,压惊的药茶备着,太医也在这院里住着,您的被褥着人暖好了,我们公子的铺盖已挪到耳室,怕打扰了王爷,若还有不妥当处,万请王爷赏话,咱们再办好些。
隔了大半个屋子,朱承昭坐在堂上,烛火明亮,淅哗作响的水声大起来,那边的屏风上映出来一个瘦细略高的人影儿,自木桶中立起:“洗好了,擦身上罢。”
音色像沾满了水气,大约泡软了,懒懒的。
想起从前抱这人睡着的那几晚……
这样的寒夜里,本是浑身发寒,刺骨心凉,屋里的铜炉火笼不起作用,因想起那时,倒突然暖了一下,
“不必这样麻烦,没得本王一来,你们就撵小子似的把他撵了,这让人怎么想?宁都统的府邸,你们小主子是主,本王是客,没有主人睡耳房,客人睡主人床的道理。”啜口茶,神色明明带笑,温温稳稳的,却看不出实地情绪:“知道你们怕委屈了本王,夜间本王同他同睡在内室便可,这里内室床上……本王瞧着也没那样不宽敞,何如?”
“…………”那妇人将他好色断袖名声想起,又想起自家小主人颜色好,福了一礼,但笑不语,也不下去,也不答应。
是个软钉子。
朱承昭更笑,偏他越笑时,眼里越寒,喃喃:“也是,这天下……就没有不疑我的……”
沉下声,冷道:“你有空……去问问你家小主子,或问问你老爷,从前不是没有见过,本王竟对他做了什么?”
那妇人忙跪下:“这是哪里的话!奴才低贱货色!哪里敢疑王爷!”
稳下,先夸道:“都听王爷的,素来闻听王爷宽和正直,平易近人,今日一见,果真如此。”
“本就是为您睡得舒适,我们小主子夜间睡觉爱活动不老实,怕冲撞了您,现在瞧见了,全是我们这些人心眼小没见识,白糟蹋好人,即这么说,都听您的,万求王爷您宽恕则个,别同我们这样没见识的小人庶民一般见识。”
想也是,自己疑人偷斧,心思太重,外头人不知道,她们也不敢传,内里却是知道小公子本是平成王养在外头,两人本就不分明,因着前王妃娘娘如今家里的秦小姐醋火大,才闹出事,在街上让认出来,若从前有心冒犯过,按老爷疼公子这劲儿,无论平成王,便是天王老子也能拉他下马,那邱家之事不是例子,大儿死在牢里,堂堂兵部尚书邱平危因曾克扣漠河军饷被革职查办……何况就算是他有那个心,老爷如今在朝中之势,他又何敢!
这样的事这样的人,从前不知忍了多少,奈何今夜像是多年装起埋在地下忘记,打开才见酿坏了好好一坛酒,皮笑肉不笑,放下茶碗道:“你先如此说,是专要本王不能和你见识,若是本王………”
正这时,一阵香风忽地暖到身前,使人心开眼亮之时,陈乖宝早扑到他一旁坐下,笑眯了眼:“好啊!俺俩个一块儿睡,你今天好,又没喝酒,不会吐俺一身。”
他像是很高兴,极热情,自打荷花收留他一段时间,又给他吃过□□,便大改初见的敌意,用有奶便是娘形容大抵过分,不过也浅显是这个意思,白天正叫他吓过一回,夜间又习惯跟人一块儿睡,从前有他哥,如今他哥没了,爱妹也叫人撵了,却正好他来,如何不高兴,已听见声音许久,好容易候人给他穿上衣裳,头发太长,炉前躺在榻上几人擦也难干,烦起来便拨开众人,出来寻他。
朱承昭面上的冷冽之意稍消,淡淡笑了。
打了个茬,那妇人实松口气,见如此,紧着命人吹了外头几盏灯,带人下去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
一夜清冷漆黑,大约人静风催之时,满室静谧,只有怀里人均匀的呼吸声,时不时拱拱他贴近,有一声软弱地梦呓。
夜不能寐的只有朱承昭。
在这样漆黑的夜里,他睁着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