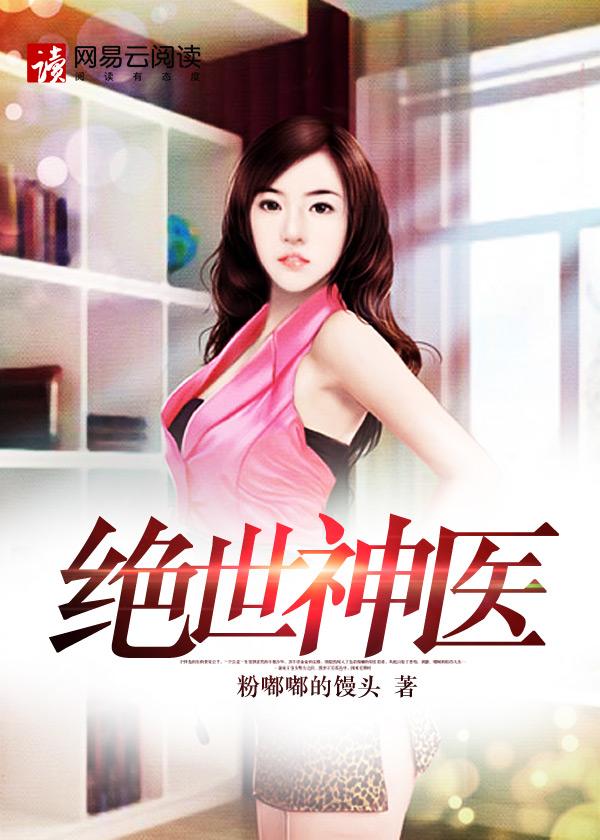文海阁>在下张梁,乃留侯之后 > 第68章 毋极清谈安顿流民返曲阳2(第2页)
第68章 毋极清谈安顿流民返曲阳2(第2页)
崔琰的笑声戛然而止,脸上掠过一丝凝重,他略作沉吟,眉头微蹙,思索一小会儿后,脸上重新神采飞扬,甚至比方才更添了几分笃定与自信!
“无妨!”崔琰用力一拍胸膛,声音斩钉截铁,“我崔季珪,不正是党锢之后才蒙恩师收入门下的么?”他眼中闪烁着智珠在握的光芒,“我稍后就修书两封,请成国(刘熙)与子尼(国渊)两位师兄代为美言,张郎君有如此经世致用之思、惊才绝艳之文,更兼心向郑学,其志可嘉!我相信,恩师若知张郎君才志,定会同意!”
见崔琰胸有成竹,众人便不再多言,话题自然流转到文事之上。
甄逸此时珍而重之地从绢布包裹中,取出张梁带来的七尺纸,向众人展示:“诸位请看,此乃张郎君新近研制的留侯纸,较之蔡侯纸,质地更匀,更宜着墨。前番张郎君也曾赠纸于我,可惜甄某一时技痒,竟悉数给糟蹋完了。”
他略带自嘲地笑了笑,“今日听闻苏家主言及张郎君在毋极,这才央他邀约,一为流民车马,二来嘛,实是心念此纸,一日不写便觉手痒难耐。”
崔琰取过一张,指尖细细,感受着那绵韧润柔的质感,抬眼看向甄逸,语带调侃:“仲道兄,今亲迎于大门,怕是有五分诚意,是冲着这留侯纸来的吧?”
甄逸但笑不语,算是默认,除了张梁与魏超,其余诸人皆好奇地取纸细观,啧啧称奇。
“留侯纸之妙处,你等一试笔便知!”甄逸吩咐侍女研墨备笔,随即转向张梁,笑容可掬,“张郎君,甄某有一不情之请……”
话音未落,便被崔琰截断:“既知是不情之请,那不说也罢!”引得在座几人都忍俊不禁。
甄逸佯怒瞪了崔琰一眼:“好你个季珪!还未成同门,便护起短来了?”他不再理会崔琰,对张梁恳切道:“甄某想请郎君留下两幅墨宝——就写那‘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’,以及‘文以载道,言以足志’两句,以作我书房里的镇斋之宝!”
此言一出,崔琰与刘惠立刻不依不饶起来。
“两句皆被你一人独得,我等岂非空手而归?”
“仲道,贪多嚼不烂,你只能择其一!”
厅中顿时起了小小争执,最终,甄逸得了长句,刘惠心满意足地分走了短句。崔琰则如愿以偿,索要了那令他击掌相和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
一首不曾说话的张钧,此时也含笑上前相邀。得知他即将入朝为官,魏超灵机一动,向张梁建议道:“三郎,何不将你那日劝说田先生出山时所言,书赠给张兄?我看就正合其志!”
张钧闻言,眼中精光一闪:“田先生?莫非是辞官归隐的钜鹿名士田元皓先生?”
魏超点头,“正是!前番司隶有疫,大批流民涌入钜鹿,我曲阳城接纳了万余流民。彼时恰逢县令外出,县丞县尉新旧交替,县中无人主事。我三人便亲往田先生隐居处,恳请他出山代掌政务,以安黎庶。”
“哦?”张钧兴趣更浓,“不知是何等金石之言,竟能打动田先生?愿闻其详。”
魏超神色肃然,一字一句,清晰有力地吟诵道: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”
张钧听闻此句,整个人瞬间肃立,手上毫毛倒竖,仿佛有电光在背脊处通过!他即将踏入的,正是那庙堂之高——郎中一职,虽非显赫,却是天子近侍,出入宫禁,参赞机要,乃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清要之位。
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——这八个字,如同一柄重锤,狠狠砸在他因升迁而有些激荡的心上!它提醒着张钧,紫绶金章并非终点,而是以忧民之实,践履忠君之志的起点。
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——此句更如洪钟大吕,在他心头震响。田丰先生何等人物?宁折不弯,因首谏不容于时而归隐江湖!其“忧君”之心未死,故能被此语打动出山。这忧君不是阿谀之态,实乃对社稷安危、国运兴衰的深切挂怀。
张钧深吸一口气,仿佛要将这两句话,刻入肺腑骨髓!他整理衣冠,身姿挺拔如松,向着张梁郑重地一揖,“张郎君此言,字字如金玉坠地,句句似风雷激荡!钧不日将赴郎署,定将此言悬于座右,朝乾夕惕,夙夜匪懈!身居禁中,必思黎庶之艰难;他日白衣,亦怀家国之兴替!此语,非仅劝田公出山,更是钧点明前路之明灯!钧,深谢郎君赠言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