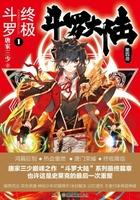文海阁>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> 第621章 战忽这回要战恐(第1页)
第621章 战忽这回要战恐(第1页)
哐当哐当~
高铁在铁轨上飞驰,商务车厢内,祁讳看着剧本和拍摄计划。
这回不是《人民的名义》了,而是《红海行动》的相关。
从沙漠回来也才仅仅五天,他就有些生疏了。
要不说拳不离手。。。
雨水顺着窗玻璃蜿蜒而下,像一道道未干的泪痕。林浩然站在办公室窗前,指尖还残留着方才关闭文档时那一瞬的颤抖。马占奎最后那句话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:“总有一天,会有人来找我们。”而现在,他就是那个“人”。
他缓缓转身,目光扫过墙上那幅地图??红点密布,如星火燎原。每一个坐标背后,都是一段被风雪掩埋的记忆,一群沉默多年的身影。他们不曾留下名字,却用血肉之躯铺就了这个国家向前奔跑的轨道。
手机震动起来,是老周发来的消息:“云南那边的地质雷达扫描出异常空腔,位置在澜沧江桥基正下方,形态疑似人工加固结构。初步判断,可能有未记录的施工避难舱。”
林浩然心头一紧。那枚铁道兵徽章上的日期??1971年10月8日,正是当年桥基塌陷事故发生的第二天。官方档案记载,三十七名工人全部遇难,无一生还。但若真存在避难舱……是否意味着,有人曾活下来?
他立刻拨通视频会议系统,召集“寻光行动”核心团队。五分钟后,屏幕亮起,小李、老周、地质专家陈工、还有刚加入不久的张秀英,全都准时上线。
“我要去云南。”林浩然开门见山,“不是调查,是救援??哪怕只有一丝可能性,我们也得试。”
张秀英坐在镜头前,神情安静却坚定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,那是她父亲马占奎生前最爱穿的款式。她轻声说:“林老师,我想跟您一起去。如果那里真的有人……哪怕只剩下一具遗骸,我也想替他们说一句‘我来接你们回家了’。”
会议室一片沉默。最终,所有人都点头同意。
三天后,队伍抵达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,澜沧江支流峡谷深处。这里山势陡峭,云雾缭绕,一条废弃的老铁路线依崖而建,锈迹斑斑的钢轨早已被藤蔓吞噬。当地村民说,几十年前常能听见半夜传来敲击声,像是有人在地下敲打铁管求救,可每次派人搜查,都一无所获。
探测设备架设完毕后,陈工指挥无人机携带微型钻探机进入预判空腔区域。随着钻头缓缓深入岩层,监测仪上的波形图开始剧烈跳动。
“有空气流动!”小李惊呼,“内部气压稳定,含氧量接近正常值!这不可能……封闭五十多年还能维持生命环境?”
更令人震惊的是,在钻孔贯通瞬间,接收器捕捉到一段极其微弱的电子信号??断续的摩尔斯电码。
老周迅速解码,声音沙哑地念出来:“SOS……K-7舱……幸存者六人……食物耗尽……请转告家人,我们没有逃跑……我们守到了最后一班列车通过……”
全场死寂。
林浩然猛地站起身,冲到操作台前亲自调校频率。他知道,这不是幻觉,也不是残响。这是实时信号!意味着,至少在这片地下世界中,某种能源装置仍在运行,而它所承载的信息,是刚刚才发出的!
“准备竖井挖掘!”他果断下令,“启用‘千灯计划’应急通道,请求军方支援重型掘进设备和生命维持系统。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打通通道!”
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,成了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战。重型机械无法运抵,只能依靠便携式破岩钻和人工轮班作业。暴雨连绵不断,山路泥泞不堪,补给几乎中断。但没人退缩。
张秀英主动承担夜间值守任务。她坐在探测仪旁,耳机贴耳,一遍遍播放那段摩尔斯电码录音。她说:“我爸当年也是这样守着引信线路,等最后一声爆破响起。我现在替他听着,也替所有没等到回音的人听着。”
第四天清晨,钻头终于穿透最后一层岩石。
一股温热的气流喷涌而出,夹杂着淡淡的机油味和……人的呼吸声。
探测摄像头缓缓送入洞穴,画面传回平板??
一个狭长的金属舱室静静卧在地下四十米处,墙壁布满锈蚀管道,顶部悬挂着几盏靠蓄电池供电的应急灯,其中一盏还在微弱闪烁。舱内整齐排列着六张行军床,床上覆盖着泛黄的毛毯。角落里堆着空罐头盒、笔记本、一支手电筒,以及一面褪色的红旗,上面写着:“铁道兵第七工程队??誓死守住桥基!”
而在主控台前,坐着一名老人。
他背对镜头,身穿一件破旧的军绿色大衣,头上戴着一顶棉帽,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,仿佛只是睡着了。但他脚边的发报机指示灯仍在规律闪烁,说明直到不久前,他还在发送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