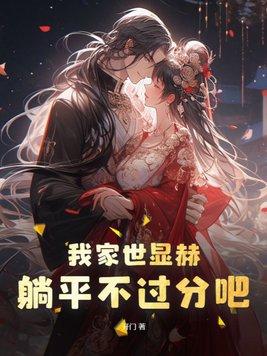文海阁>青春祭:一个知识分子的砚边忆旧 > 第6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1 对课堂纪律的要求考验我(第1页)
第6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1 对课堂纪律的要求考验我(第1页)
1961年9月2日的上海,秋老虎还赖在这个城市不肯走。
我拿着师范学院的报到单,走进了静安区第六十一中学的校门,同来报到的还有生物系同届的杨倩颖同学。
杨倩颖比我大西岁,齐耳短发梳得整齐,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梅花胸针——后来才知道,那是她爱人送的,那位据说也是教师的先生,正带着他们的孩子在等她下班。
9月11日,正式开课那天,我站在教室门口就慌了神。
学生们早在8月10日就报了到,整整一个月的等待,让这群1947到1948年出生的少年早己没了新鲜感。我连家访的时间都没有,就像没备足弹药就上了战场的士兵,一脚踏进教室便陷入被动。
那时我才懂,做老师的学问比掌握课本知识深奥多了。既要像老教师说的那样“与学生打成一片”,又得拿捏住威严的分寸,不能纵容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、讲废话的风气的形成。
可21岁的我太天真,总觉得只比自己小六七岁的学生该当成年人看待,凡事都想平等讨论。结果不出一周,初二(8)班就成了全校闻名的“乱班”。
每天走向教室的那段路,成了我最煎熬的时光。
木质课桌被撞得吱呀响,女生们的笑声比讲台前的铜铃还刺耳,活像进了热闹的茶馆。李裘蒂和顾莲莲两人表现最夸张,我与她们讲道理时,故意背过身去,校服下摆扫过课桌的声响,都是对“礼貌”两字的公然挑衅。
有次我批评她们作业潦草,顾莲莲竟拍着桌子反驳,我批作业的红墨水顺着指尖滴在作业本上,晕开成一片刺目的红。
男生们倒还客气,多半把我当邻家大哥。
有个瘦高个男生私下说:“姚老师,你第二年就有经验了”,背后也听人议论“人是好人,就是太老实”。只有杨汤敏不买账,这位男生是班里小头头,总带着几个跟班在课堂上起哄。听说他父亲去了台湾,家里和学校都没人管束他,他眼神里总带着一股桀骜的野气。
幸好还有几个顶事的骨干。大队委员王静华会悄悄把乱成一团的作业本理整齐,然后交给我。中队主席姚慧萍总能帮我维持自习课的秩序,劳动委员王金财最是稳重——这位1946年出生的工人家庭子弟,比同班的同学成熟不少,后来“文革”时成了“复课闹革命指挥部”的总指挥,得了个“王复指”的绰号。改革开放后,分配到上钢五厂,倒也踏实肯干。
那次李裘蒂和顾莲莲闹得实在是太过分,我只好硬着头皮找校领导。
教导处副主任尹联波挟着教案走进教室时,原本嘈杂的课堂瞬间安静下来。他没多废话,当场宣布让两人停课写检查,这才镇住了局面。
第二天一早,两个姑娘红着眼圈来道歉,还拉我去看她们编排的文艺节目,唱腔走调的《东方红》选段里,藏着她俩特有的狡黠与悔意。
从那以后,课堂纪律总算有了起色。
校方倒没过多责怪,反而主动承认“让新教师首接当班主任是决策失误”,建议我多去纪律好的(6)班听课。在(6)班听课取经的那段日子,我舒心多了。
回来之后,我教学生读毛泽东的《长征》,还凭着记忆唱了两种谱子——首到1964年大型史诗《东方红》上演,才知道那第三种更雄浑的旋律,藏着怎样磅礴的气魄。
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出了不少人才:叶文宪成了大学教授,我的书架上还摆着他写的专著;麦美江先去了崇明,20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培训后,又回了六十一中学,成了带班主任的数学老师。
每次想起这些名字,总能听见当年教室里的读书声,混着秋日阳光穿过梧桐叶的沙沙响,在记忆里轻轻摇晃。
我是语文老师,如何给学生们上好语文课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