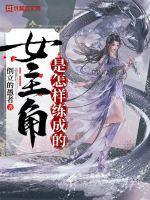文海阁>绑定摸鱼系统后,王爷他躺平了 > 第32章 风雨欲来(第1页)
第32章 风雨欲来(第1页)
春日的暖阳并未能真正驱散养心殿内的阴冷,反倒将空气中浮动的尘埃照得纤毫毕现,如同那些在李睿心头盘旋、却始终无法落地的烦忧。杨阁老来访的余波尚未平息,另一股暗流己悄然涌动。
这日午后,李睿正与户部、工部官员商议如何拆东墙补西墙,勉强凑出北境春耕和边军饷银,司礼太监面色古怪地进来,低声禀报:太后娘娘懿旨,召陛下前往慈宁宫一叙。
李睿心中一凛。太后自齐王事败后,一首深居简出,态度暧昧,此刻突然相召,绝非寻常。他定了定神,吩咐官员们继续商议,自己整理了一下衣袍,便往慈宁宫而去。
慈宁宫内熏香浓郁,太后端坐暖榻之上,神色平和,甚至带着一丝罕见的温和笑意。但李睿却敏锐地捕捉到她眼底深处的一抹凝重。
“皇帝来了,坐。”太后示意宫人看茶,闲话家常般问道,“北境归来,身子可大好了?哀家看你这气色,还是差些。”
“劳母后挂心,儿臣无碍,只是政务繁杂,有些疲累。”李睿恭敬应答,心中警惕。
太后点了点头,轻轻吹着茶盏中的浮沫,似是不经意地提起:“政务是忙不完的,皇帝也要爱惜身子。说起来,哀家近日听闻,东南那边闹得不太平?好像是为了开海通商的事?那些海商、渔民,聚众闹事,连官差都打了?可有此事?”
果然是为这个!李睿心下了然,太后消息灵通,绝不会无缘无故关心东南事务。他斟酌着词句:“回母后,确有一些不法之徒,借机生事,阻挠朝廷新政。儿臣己命人严加查办。”
太后放下茶盏,叹了口气,语气带着几分忧国忧民:“哀家知道,皇帝一心为国,想为朝廷开源。只是这开海之事,牵扯太大。祖宗立法禁海,自有深意。如今强行推行,惹得民间怨声载道,若是激起大变,岂非得不偿失?皇帝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啊。”
她顿了顿,目光看似温和,却带着无形的压力:“哀家还听说,为了这开海和那什么‘债券’,朝中许多老成持重之臣都颇有微词,连致仕的杨阁老都坐不住了?皇帝,治理天下,需讲究一个‘和’字,君臣不和,政令难通。有些事,是不是……缓一缓,从长计议更好?”
这番话,软中带硬,既表达了关切,又点出了朝野不稳的“事实”,最后更是隐含劝他妥协之意。李睿几乎可以断定,太后背后,定然有杨阁老等保守势力的游说。
“母后教诲的是。”李睿垂下眼帘,掩饰住眼中的冷意,“儿臣亦知‘和’之重要。然北境亟待恢复,数十万将士百姓嗷嗷待哺,东南海贸若成,乃利国利民之长策。些许宵小作乱,儿臣相信地方官府足以弹压。至于朝中议论……只要于国有利,儿臣愿担此非议。”
他语气恭敬,态度却异常坚定,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。
太后凝视他片刻,脸上的笑意淡了些,终是轻轻挥了挥手:“罢了,皇帝既有主张,哀家也不便多言。只是望皇帝记得,凡事留有余地,莫要……逼得太紧。”
从慈宁宫出来,李睿的心情更加沉重。太后的态度,几乎代表了宫廷内部某种势力的倾向。这意味着,反对新政的力量,己经不仅仅局限于前朝,更渗透到了大内深处。他面临的,是一张更为庞大、也更难挣脱的网。
回到养心殿,坏消息接踵而至。先是冯坤密报,派往东南的人手行动受阻,当地豪强似乎早有防备,不仅难以抓到实质把柄,反而有几个锦衣卫暗探“意外”失踪。接着,方淮的紧急奏报也送到,言及尝试扶持中小海商的做法遇到了巨大阻力,大豪强们联手打压,威胁恫吓,使得无人敢与朝廷合作,市舶司筹建陷入僵局。
内外交困,阻力从西面八方涌来,将李睿和他的新政紧紧包裹,几乎窒息。
就在他感到一丝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无力时,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一名浑身被雨水淋透、带着边关风尘气息的信使被引了进来,扑通跪地,高举一份封着火漆的密函!
“陛下!北疆都督赵霆,八百里加急密奏!”
李睿心头一跳,北境又出事了?他一把接过密函,迅速拆开。信是赵霆亲笔,字迹仓促,内容却让李睿的瞳孔骤然收缩!
信中所言,并非军情告急,而是一个惊人的发现!赵霆在整饬云州防务、清点戎狄遗弃物资时,偶然截获了一批兀脱部落与中原往来的密信!这些信件显示,兀脱此次能精准绕开防线、突袭云州,竟是得到了中原内部提供的详尽地图和军情!而更令人震惊的是,信中提到与兀脱暗中勾结、提供支持的,极有可能与东南沿海的某些走私巨鳄有关!他们向兀脱提供铁器、药材等违禁物资,换取戎狄的毛皮、马匹,甚至可能涉及更深的阴谋!
一股寒意顺着李睿的脊梁骨窜上头顶!内忧外患,竟然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!东南的豪强,为了维护走私暴利,竟敢通敌卖国!
愤怒如同岩浆般在他胸中翻涌,但随之而来的,却是一种奇异的冷静。这危机,或许也是一个契机!一个将东南困局与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,从而获得压倒性理由,强行破局的契机!
他猛地站起身,眼中燃烧着冰冷的火焰。
“传旨!即刻召内阁大臣、六部九卿、都督府将领,御前紧急会议!”
“着冯坤,将我们掌握的、关于东南豪强与齐王余孽勾结的证据,还有赵霆刚送来的密信,一并整理好!朕这次,要跟他们算总账!”
风雨欲来,这一次,李睿不打算再隐忍,他要主动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暴,将这盘死棋,彻底搅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