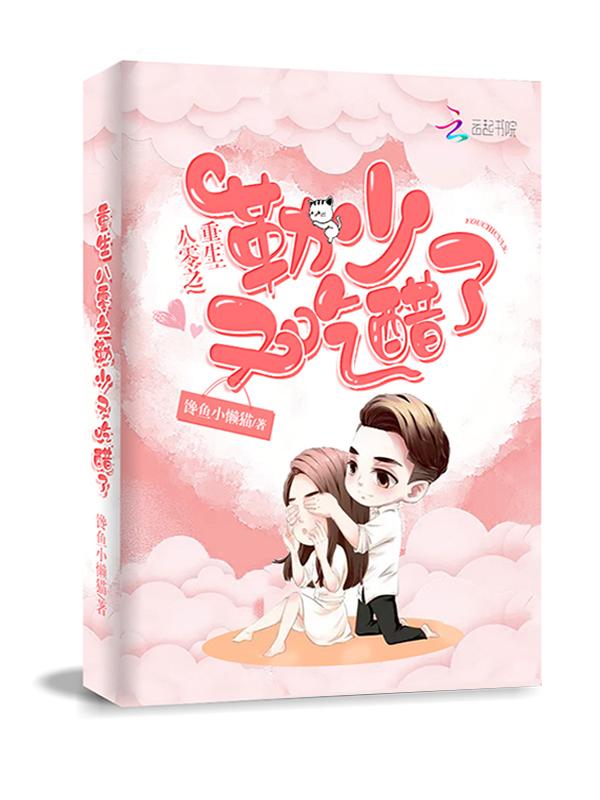文海阁>扶云直上九万里 > 1寻找李凭云1(第4页)
1寻找李凭云1(第4页)
若问科举于她最大的意义是什么?此时此地,她可以肯定地给出答案:逃避成为种马家的母马。
现在她远赴太和,同裴瑯正好眼不见心不烦,想到很长一段时间不用面对花心的未婚夫,她的语气也不觉温柔了些。
“裴瑯,这里不算高,而且地上都是沙土,摔下去,肯定摔不死的,顶多将我摔成伤残。”
裴瑯以为赵鸢是在顾左右而言他,他道:“鸢妹,你是不是还在生我跟阿愉的气?”
“裴瑯,我是生气,可我不会因自己生气,就让你把她逐出府。阿愉伺候了你这么多年,你将她逐出府,她又能去何处?”
裴瑯也不知赵鸢是说真心话,还是说反话。
“别气了。”裴瑯生了一张招桃花的面容,他服软撒娇,哪个姑娘都受不了。
赵鸢索性背过身,不去看他。
“鸢妹,为了给你赔礼道歉,也为了祝贺你迈入仕途,我准备了一个礼物,路上没来得及送你,此情此景,倒是适合赠礼。”
“不必了,裴瑯,你送不送我礼,日后你我都要成婚,何必铺张。”
“你都不问是什么,就拒绝么?”
赵鸢心意已决,不论裴瑯送什么,她都不会被轻易被他讨好。
“嗯,我不想知道。”
“若是和李凭云有关呢?”
果然,但凡涉及“李凭云”,赵鸢就连话都不会说了。
他从腰间锦囊出取出一枚方正黄梨花木印,“这是我在驿馆小二那里得来的,说是李凭云亲手所刻。”
裴瑯点燃一簇火,照亮手上那枚掌心大小的木印。
赵鸢转过身,从他手上拿起木印,瞧了瞧刻字的地方,印的是“闲云野鹤”四字。
赵鸢不信这枚印章是李凭云刻的。
“三年前科举后,长安再也不闻其名,今年春试出了考场,我听几个南方来的贡生谈起他,说他瞧不上官场龃龉,辞了进士身份,去了南方,怎么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。”
裴瑯道:“你不知道道听途说不可信么?。那可是状元郎身份,多少人从童颜熬到鹤发,蹉跎一辈子,也中不了进士,怎会舍得下状元身份,离开仕途,闲云野鹤?”
裴瑯不知道自家未婚妻看起来老实,脑子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她备考科举,每夜入睡的流程大抵如下:
先读一遍李凭云的文章,再写自己的文章,做完读书人该做的事情,开始做梦。
在她的梦里,李凭云这三个字时而是魏晋美男,时而是三国谋士,时而长得好看,时而比上一次长得更好看。
她完全忽视了对方是会吃喝拉撒的真人,在她迂腐的小脑袋里,近乎狂热地爱慕这对方。
她坚定认为自己的梦中人个不屑仕途的闲云野鹤,而非裴瑯所说的庸俗之辈。
想起自己素未谋面的心上人,赵鸢不禁高傲起来:“李凭云,他不一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