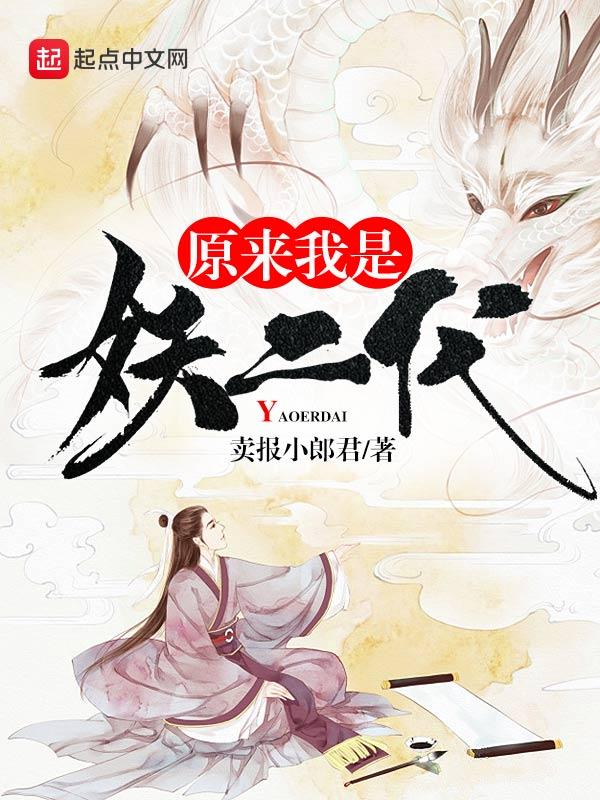文海阁>魅力点满,继承游戏资产 > 第七百一十章 纯情女大2018(第1页)
第七百一十章 纯情女大2018(第1页)
唐宋的身影,跟随着那辆缓缓进站的31路公交车,在站台上挪动着。
晚上六点半的燕景天城外,正是人流高峰。
下班的白领、提菜的阿姨、学生与外卖骑手,交错而行,灯光在地面上流动闪烁。
穿着。。。
沈玉言醒来时,窗外雪已停。晨光落在窗台上,像一层薄薄的银箔,映得房间通透明亮。她没有立刻起身,只是静静躺着,任由梦境的余温在胸口缓缓流淌。那个教室、那句关于雨天的话,仿佛不是来自记忆,而是某种真实的低语,从时间的缝隙里悄然渗出。
她终于明白,有些告别不需要声音,也不需要回应。它发生在心与心之间最安静的震颤中,像一粒种子沉入泥土,不求再生,只为完成一次完整的坠落。
起床后,她泡了杯热茶,走到书桌前翻开那本新买的笔记本。昨夜写下的那句话依旧清晰:“有些记忆,注定只能走一遍心,不能存一次盘。”她盯着这行字看了许久,忽然拿起笔,在下方添了一句:
**“而真正的铭记,是让它成为你呼吸的一部分。”**
手机震动起来,是林昭发来的消息:“今天下午三点,新课程试讲,来吗?”
她回了一个“好”字,顺手将U盘的照片发了过去??那是昨天她去文物部门办理封存手续时拍下的。U盘被装在一个黑色绒布盒中,标签上写着“非访问级,永久封存”,旁边还附了一张手写卡片复印件,正是陈技术员信里的最后一句:“生命总会找到新的出口。”
几分钟后,林昭回复:“我把它打印出来,贴在教室墙上。”
沈玉言笑了笑,把手机放下,开始整理衣橱。冬天的衣服挂得满满当当,她在最深处翻到一件旧毛衣??灰蓝色,领口有些松了,是五年前唐仪送她的生日礼物。那时她们还在为【归巢】的初代算法熬夜调试,唐仪一边织一边抱怨:“你说人脑为什么不能像代码一样,删掉bug就能重跑?”沈玉言记得自己当时笑着说:“因为那样就没人会为你哭。”
她轻轻抚摸着毛衣,指尖触到一处细微的结。翻过来看,才发现袖口内侧用细线绣了个小小的“T。Y。”,针脚歪歪扭扭,像是赶工完成的。那一刻,她忽然觉得这件衣服比任何数据都更接近唐仪的存在。它承载的不只是温度,还有笨拙的爱意、未说出口的依赖,以及那些深夜实验室里shared的沉默。
下午两点四十分,她穿上这件毛衣,出门前往学校。
天空依旧清冷,但阳光明媚。校园里的积雪已被清扫干净,梧桐树干上挂着几串红灯笼,是新年临近的预兆。感知与记忆研究中心的教学楼前立着一块新铭牌,字体简洁有力。门口已有学生陆续进入,不少人手里拿着打印好的《唐仪宪章》节选。
林昭拄着拐杖站在讲台边,穿着一件深灰色大衣,脸色比前些日子好了许多。见到沈玉言进来,他微微一笑,递给她一杯热咖啡。
“紧张吗?”他问。
“有点。”她说,“毕竟这是第一堂正式课。”
“可你已经讲了整整一年。”他轻声说,“从纪念馆开始,到日内瓦,再到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面前。”
教室坐满了人,除了本校研究生,还有外校旁听的教师和媒体记者。黑板上方挂着一幅投影,显示今天的课程标题:《哀伤的技术边界??当科学遇见死亡》。
沈玉言走上讲台,目光扫过全场。没有人说话,连翻纸的声音都格外轻柔。
“我们今天不讲理论框架。”她开口,“我想先放一段录音。”
她点击播放键。
音响里传出一个稚嫩的女孩声音,带着轻微的电流杂音:
>“妈妈,别哭。我走了以后,春天还是会来的。”
教室陷入一片寂静。有人低头,有人闭眼,前排一个女生悄悄抹了眼角。
“这段话,”沈玉言继续说道,“原本不属于任何研究项目。它是某个临终病房里,一位十二岁女孩对着录音笔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后来被家属捐赠给伦理数据库,编号D-0739。三年前,它曾被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试图用于‘情感模拟人格’训练模型,理由是‘让失去孩子的父母获得慰藉’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沉稳:“但我们阻止了。不是因为它太真实,而是因为它太珍贵。一旦被复制、被程序化、被无限回放,它就不再是那个孩子最后的温柔,而成了消费悲伤的商品。”
台下有人举手提问:“但如果家长自愿使用呢?哪怕明知是假的,只要能缓解痛苦,难道不行吗?”
“可以。”沈玉言点头,“但必须清楚代价。每一次回放,都是对真实记忆的一次覆盖。大脑会逐渐混淆‘听到的声音’和‘曾经拥有的声音’。最终,他们记住的不再是女儿的笑容、脾气、撒娇时的小动作,而是一个永远甜美、永不争吵的虚拟影像。”
她看向林昭,“林老师曾在一份未发表的论文里写道:‘哀伤的本质,是一场与过去的谈判。’如果我们用技术跳过这场谈判,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走出门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