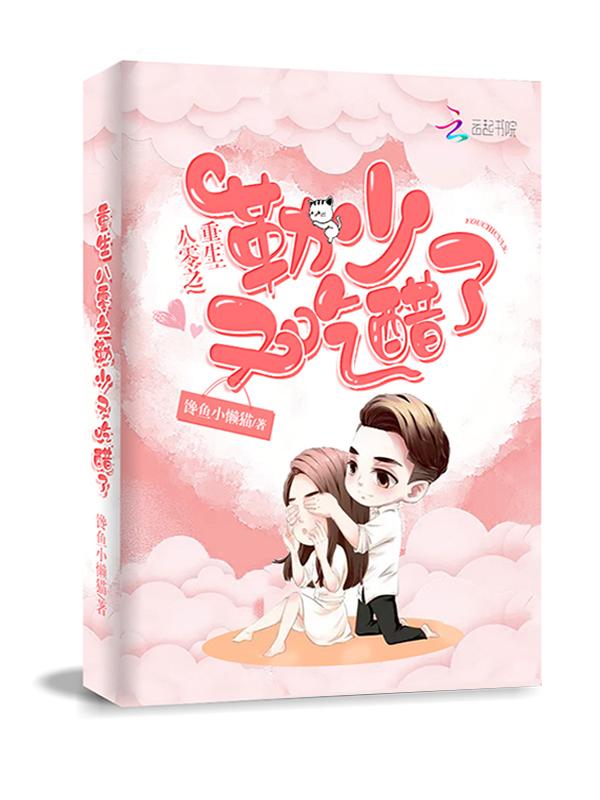文海阁>我真没想下围棋啊! > 第四百九十六章 一桩六月飘雪的冤案(第2页)
第四百九十六章 一桩六月飘雪的冤案(第2页)
**我要上学。**
第二天清晨,全村人都来了。他们带来鸡蛋、土豆、腊肉,还有几个孩子怯生生递上的作文本。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说:“我家孙子三年没叫过我一声奶奶,昨晚上他抱着我说,‘奶,我梦见你在听我说话’。”
我们当场决定,在马家坪试点“倾听学校”的第一个正式校区。不用重建校舍,就在原有粮仓基础上加固屋顶,铺设防潮层,安装太阳能供电系统。志愿者陆续从各地赶来??有心理咨询师、特教老师、社工,甚至有一位退役围棋职业选手,主动提出义务教授“情绪棋课”。
一个月后,“马家坪声音之家”挂牌成立。开学第一天,我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:每个孩子都要完成三件事??
第一,走上讲台,说出自己名字;
第二,在棋盘上落下属于自己的一颗棋子;
第三,对着录音笔说一句“我一直想说,却没人听的话”。
有个六岁女孩站在台上,攥着衣角,足足五分钟没出声。最后她跑下来,趴在沈砚之耳边说了三个字:“我想妈。”
我们查访得知,她母亲因精神疾病被送进福利院,已有五年未见。当天下午,我们就联系当地民政部门,启动探视程序。
与此同时,“声音漂流瓶”项目迎来第1000位参与者。一位内蒙古牧区的初中生寄来一段蒙语录音,讲述自己因口吃被同学嘲笑,曾三次尝试自杀。他在信中附了一张手绘地图,标注了草原上十几个散居的蒙古包,说:“这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,你们能不能来?”
我们回复:“正在路上。”
转眼入夏。某日深夜,我整理档案时发现一封匿名邮件,附件是一段加密音频。播放后,竟是一个成年男声,带着浓重鼻音:
“我是当年打孩子的那个父亲……我听了石头写的作文,整整三天没合眼。我知道我不配做爸爸,可我还是想问他,能不能……让我学着重新开始?”
我将音频转给心理团队评估,三天后安排了一次三方通话。父子隔着电话线沉默了十分钟,最后是父亲先开口:“儿啊,爸不会说话,只会动手……但我现在知道错了。你要不要,教我下盘棋?”
石头听完翻译,点点头,录了一段回音:“可以。但你要答应我,输了不能打人。”
那一刻,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和解,更像是一种血脉深处的觉醒??暴力从来不是天生的,它只是失语太久的回响。
秋天到来时,我们在贵州铜仁建起第三座“声音之家”。这一次,我们尝试引入“代际对话课”,邀请父母与子女共同参与表达训练。有位常年外出务工的父亲,在课堂上听完女儿朗读的作文《爸爸的背影》,当场跪地痛哭。他原以为孩子恨他缺席,却发现她每天都在日记里画他穿工装的模样,并写下:“我长大也要去深圳,这样就能找到爸爸的味道。”
年底,“听懂的心”年度报告发布:全年服务儿童3872人,收集有效音频日记6421条,促成家庭和解案例189起,推动地方教育部门设立“倾听课堂”试点校23所。最令人振奋的是,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发来函件,表示将参考我们的课程模型,研发全国首套“儿童情感表达指导手册”。
庆功宴上,有人提议给沈砚之颁奖。他摇头拒绝,只说了一句:“真正的奖赏,是某个孩子终于敢在夜里喊出‘妈妈,我害怕’。”
新年除夕,我们回到龙脊坳。阿?已长成亭亭少女,剪了短发,穿着校服站在村口迎接。她身后站着二十多个孩子,每人手里捧着一盏纸灯笼,上面写着一句话:
“我说话了。”
“我不怕做噩梦了。”
“我想念爸爸,但他不会再打我了。”
午夜钟声响起时,阿?举起她的灯笼,点燃引信。一朵烟花腾空而起,在夜空中炸出清晰的图案??那是一个巨大的棋盘,中央写着两个字:
**轮到。**
沈砚之站在我身边,轻声说:“你说,如果我们老得走不动了,谁来接替这条路?”
我望向那些仰脸看烟花的孩子,笑了:“你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了??光一旦亮起来,就不会再灭。”
年初七,我们启程前往新疆喀什。一位维吾尔族教师来信说,有个十四岁的聋哑女孩,近三年用手语创作了三百多幅画,主题全是“声音的模样”。她画过哭泣的脸、张开的嘴、飘在空中的文字,最后一幅题为《我想听爸爸叫我名字》。
飞机降落时,沙漠边缘的朝阳正缓缓升起。我握紧背包里的录音笔,里面存着最新一期的《听见的人》合辑。开头是小岩的声音:“今天我帮同学解开了被嘲笑的结巴难题,他说谢谢的时候,我才知道,原来勇气是可以传递的。”
下了舷梯,寒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沈砚之拍掉肩上的雪,笑着说:“这一站,可能会很难。”
“可我们早就习惯了。”我说,“毕竟,轮到我们了。”
车子驶向绿洲途中,我打开录音笔,按下录制键:
“这里是李砚秋,现在是北京时间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四十七分,我们正前往新疆喀什疏勒县塔尕尔其乡。我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,但我知道,一定有一个孩子,正在某间教室的角落里,默默画着属于他的棋盘。”
“你好,”我顿了顿,声音温和而坚定,“轮到你了。”